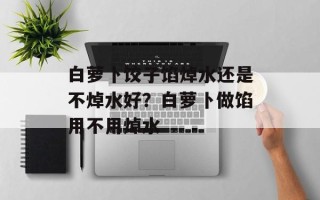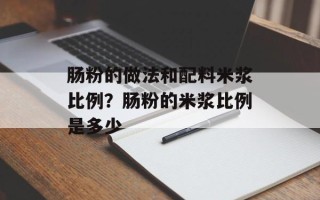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补中益气汤加减医案,31补脾胃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一、罗天益针灸医案特色探析
1、罗天益(1220—1290),字谦甫,真定(今河北省保定市)人,元代医学家,曾任太医,从李果学医多年,深得赏识。其继承李果之精华,并有所发展,汲取张洁古、云岐子父子之针灸遗法,主张针灸药并用,因证而施,著有《卫生宝鉴》等著作。《卫生宝鉴》各卷中散见大量的医案,其中采用针灸治疗者不少。本文主要根据《卫生宝鉴》中的17则针灸医・针灸经络・案,探讨罗天益的针灸治疗特色。

2、李东垣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脾胃虚则元气衰,元气衰则百病由生,刨补中益气诸方温补脾胃。罗天益在师承李杲脾胃学说的基础上,大倡灸法补脾。
3、罗天益灸法补脾之医案,其补脾基本穴为中脘、气海、足三里。中脘“引清气上行,肥腠理”,“温脾胃之气,进美饮食”。中脘为胃之募穴,六腑之会,灸中脘能温补脾胃,升提中气,开胃进食。“灸气海百壮,生化元气,滋养百脉,充实肌肉”。气海穴居脐下,为元气之海,灸之大补元气,化生气血,固表抗邪,为方中辅穴。足三里“引阳气下交阴分,亦助胃气”,“引导热气下行”。足三里为胃经合穴、胃腑下合穴“合治内腑”,灸之有补益脾胃,引阳交阴,引热下行的作用。中脘在上主升,而脾胃学说强调“升”的一面,故为方中主穴,气海居中,足三里在下主降,二穴为方中辅穴,三穴共奏温补脾胃、升提中气、培元固本、调和阴阳之效。
4、对一般的脾胃虚寒证,天益取中脘、气海、足三里治疗。如治崔云卿之胃脘当心而痛,腹痛肠鸣,饮食减少,心下痞闷,呕吐酸水,冷汗时出,手足梢冷,面色青黄而不泽,脉弦细而微诸症,罗谦甫灸上述三穴,配扶阳助胃汤治疗而愈。又如周卿子之“虚中有热”案、史候男十哥之“结阴便血”案,天益灸中脘三穴,配甘寒、甘温之剂治疗而愈。对脾胃内伤轻症,天益仅灸中脘一穴,如范郎中夫人因劳逸饮食失节,加之忧思气结,病心腹胀满,旦食则呕,暮不能食,脉弦而细,罗谦甫灸中脘,并以木香顺气汤助之而愈。对脾胃内伤重证,天益除三穴合用外,还加穴治疗,如王千户之“阴阳皆虚”,罗谦甫加灸阳辅以接续阳气,温化寒湿,兼服附子理中汤而愈。
5、罗天益在东垣甘温药物补脾的基础上,重视灸法补脾,而且补脾灸方章法严谨,进一步完善、发展了李东垣的脾胃论,同时也为针灸治疗内脏病提供了范例。
6、《素问・至真要大论》日:“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素问・异法方宜论》日:“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洌,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媾。”可见灸法的主要作用是温阳散寒。罗天益遵《内经》之旨,对阴寒内盛诸证,善用灸熨,温补阳气,通经散寒。卷二十二“腼寒治验”…抛。征南副元帅大忒木儿,年六十有八。戊午秋征南,时仲冬,病自利完谷不化,脐腹冷疼,足腼寒,脉沉细而微。天益思之:年高气弱,军事烦冗,朝暮形寒,饮食失节,多饮乳酪,履于卑湿,阳不能外固,由是清湿袭虚,病起子下,故腑寒而逆,此寒湿相合为病也。法当急退寒湿之邪,峻补其阳,非灸不能病已。先以大艾炷于气海灸百壮,补下焦阳虚;次灸足三里三七壮,治腩寒而逆,且接阳气下行;又灸三阴交,以散足寒湿之邪。并以附子等辛热之剂助阳退阴,温经散寒。调治数日,肪寒渐温,泻止痛减而愈。
7、卷十六“葱熨法治验”肛"。真定一秀士,年三十余,体本弱,左胁下有积气,不敢食冷物,得寒则痛,或呕吐清水,眩晕欲倒,目不敢开,服辛热之剂则病退。延至甲戌初秋。因劳役及食冷物,其病大作,腹痛不止,冷汗自出,四肢厥冷,口鼻气亦冷。天益思《内经》云:“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滞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又寒气客于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诸寒在内作痛,得热则痛立止。罗谦甫欲予药服之,药不得入,见药则呕。遂以熟艾约半斤,白纸一张,铺于腹上,纸上摊艾令匀。又以憨葱数枝,削成两半,铺于熟艾上数重。再用白纸一张覆之,以慢火熨斗熨之,冷则易之。初熨时得暖则痛减,大暖则痛止。至夜得睡,翌日再予对证药服之,良愈。
8、卷六“阴证治验”…”。佥院董彦诚,年跨四旬,因劳役过甚,烦渴不止,极饮湮乳,又伤冷物,遂自利肠鸣腹痛,四肢逆冷,冷汗自出,口鼻气亦冷,时发昏愦,六脉如蛛丝。天益以葱熨脐下,配以四逆汤加姜、葱。至夜半,气温身热,恩粥饮,至天明而愈。
9、以上医案虽然均为阴寒内盛之证,但因患者年龄、体质、病因、病情各异,所以在施灸 *** 上亦有所不同。患者年高气弱,足胫冷痛,脉沉细而微,罗天益认为乃因阳虚而为寒湿侵袭所致,法当峻补其阳,急退寒湿,而艾灸长于补阳,故施之以大艾炷,选气海、足三里、三阴交等强壮穴,温补阳气以退寒湿。真定秀士与董彦诚均为中年,均有腹痛不止,四肢厥冷,冷汗自出诸症,乃因阴寒内盛而致阳虚欲脱。葱熨法长于温里散寒,故罗天益选葱熨法施于腹部脐下,温里散寒,回复阳气。
10、针对邪毒入络,气滞血瘀,导致局部红肿疼痛,罗天益宗《内经》“热则疾之”,“血实宜决之”之旨,以针砭刺络放血,泄热祛邪排毒。
11、卷二十二“风痰治验”…槲。参政杨公七十有二,宿有风疾,至元戊辰春,忽病头旋眼黑,目不见物,心神烦乱,头偏痛,微肿而赤色,腮颊亦赤色。罗天益认为患者年高气弱,喜饮酒,久积湿热于内,风痰内作,上热下寒,上热虽盛,岂敢用寒凉之剂损其脾胃!宗《内经》“热则疾之”的理论,用三棱针在头上刺出紫黑血二十余处,少顷,头目便觉清利,诸症悉减,又予天麻半夏汤,数剂而安。
12、卷二十二“北方脚气治验”…狮。中书粘合公,年四旬有余,躯干魁梧。丙辰春,从征至扬州时脚气忽作,遍身肢体微肿,其痛手不能近,足胫尤甚,不能穿履。罗天益认为,此乃湿毒入络,气滞血瘀,导致足胫肿痛,遵《内经“血实宜决之”的理论,以三棱针数刺其肿上,血突出高二尺余,渐渐如线流于地,约半升许,其血紫黑,顷时肿消痛减,又以当归拈痛汤服之。是夜得睡,翌日而愈。
13、卷二十二“病有远近,治有缓急州 36‘。征南元
14、帅不游吉歹,年七旬,丙辰春冬征,因过饮酒醴,遂咽嗌肿痛,耳前后赤肿,舌本强,涎唾稠粘,欲吐不能出,言语艰难,夜不得卧,腹痛肠鸣,泄泻。罗天益认为患者咽嗌肿痛,耳前后赤肿而标急,急则治其标,遂砭刺肿上,紫黑血出,顷时肿势大消,然后用异功散等药调补脾胃以治本,数服而愈。
15、卷二十三“上热下寒治验”…367。姚公茂六十有七,宿有时毒,至元戊辰春,因酒病发,头面赤肿而痛。耳前后肿尤甚,胸中烦闷,咽嗌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胫尤甚。罗天益诊为上热下寒。根据《内经》“热胜则肿”,《难经》“蓄则肿热,砭射之也”的理论,谦甫遂于肿上刺约五十余刺,其血紫黑如露珠之状,顷时肿痛消散。又灸气海、足三里,退足胫之寒,助之以既济解毒汤,不旬日良愈。
16、针对上述诸案之阳证、热证、实证、痛证,罗天益主张针砭放血,泄热排毒,通络止痛。而对于阴证、寒证,罗天益则主张施以燔针开决排脓,如王伯禄之附骨疽…181,或以锐针刺其肿上,按出其恶气以排毒,如段库史之疠风… 5,充分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
17、罗天益虽然非以针灸名世,而是以中医内科为专长的中医大家,但是,他在针灸学术上的造诣亦颇为深厚。其原因一是他的经典之功底扎实,深得《内经》、《难经》针法之精华;二是他继承了脾胃学派开山鼻祖张洁古、云岐子父子的针灸学术;三是他经常与当时的针灸大师窦汉卿、忽吉甫切磋医术,交流心得,深得针灸名家之真传。其针灸医案除以上引述之外,还有采用云岐子刺十二井穴。针灸肩井,灸尺泽,服加减冲和汤治疗张安抚之“风中腑兼中脏治验”…;宗《内经》经旨与沽古经验,取天柱、灸照海与申脉,服沉香天麻汤治疗魏敬甫之子的“惊痫治验”…;灸中庭穴,服当归四逆汤治疗赵运使夫人的“疝气治验”等。
二、补中益气汤该如何用
补中益气汤,最早出自李东垣所著的《内外伤辨惑论》一书,被后世医家推崇至极。明代医家张景岳评价道,“补中益气汤,允为李东垣独得之心法。”而今日,善用补中益气汤的医者日少,初涉临床的医生使用补中益气汤每每会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感觉。为什么?重新认识补中益气汤,重新审视李东垣笔下的补中益气汤,也许有益于临床。辨证:治内伤脾胃始得量轻效宏读《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可以看出,补中益气汤治疗内伤脾胃之证,是“始得之证”,临床表现可以和外感风寒之证相类同。其病因为“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喜怒忧恐,劳役过度”。病机为“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肝,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治则为《内经》所说的“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具体治法是“惟当以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方中“须用黄芪最多”,但仅用“五分”,“劳役病热甚者一钱”,他药各用“三分”。折合成现代用量,一剂药总剂量仅为10克左右。服用 *** 是“早饭后温服”。方中黄芪、炙甘草配伍升麻、柴胡,重在“实其表”,“不令自汗,损其元气”;人参、炙甘草重在“补脾胃中元气”;白术除用其“甘温”之外,重在用其“苦”;橘皮“导气”,当归酒洗“和血脉”。辨脉:右脉大于左脉数中显缓李东垣临证注重辨脉,对外感、内伤之别首列“辨脉”,并且认为辨脉已足够,“以此辨之,岂不明白易见乎。”之所以《内外伤辨惑沦》中又列辨症候,是“但恐山野间卒无医者,何以诊候,故复说病证以辨之。”李东垣在“辨脉”中提到“内伤饮食,则右寸气口脉大于人迎一倍,伤之重者,过在少阴则两倍,太阴则三倍,此内伤饮食之脉。”“若饮食不节,劳役过甚……气口脉急大而涩数”等,尽管这里对脉象的记述似有杂乱之嫌,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右脉大于左脉,或脾脉独大于其他部位脉,并且见数脉时可“数中显缓”。这一点对于使用补中益气汤是很有临床意义的。还有,李东垣从反面论述了有一部分脉象是不可以使用补中益气汤的。方后“四时用药加减法”中,在治腹痛时提到:脉弦不可用,当用小建中汤;脉沉细不可用,当用理中汤;脉缓不可用,当用平胃散。从脉象鉴别方证,简单而实用。从李东垣笔下可以看到,补中益气汤的适应病证是非常广的,既可治内伤病,也可以治外感病;方药加减(主要是加药)是极其灵活多变的,补药、泻药、寒药、热药都可以加用,不拘一格。但万变中有其不变的根本,也就是适应症只能是“内伤”(外感病也是在内伤基础上的外感),病脉主要出现在右关,病变的主要病位在脾胃。加减:不解原意易坏事张元素立方“非为治病而设,此乃教人比证立方之道,容易通晓也”,作为张元素的弟子,李东垣深受其影响,所有方剂皆为“从权而立”,也就是重在教人立方之法,而不是传授他人所谓效方、验方。补中益气汤方后有一系列加减法及较大篇幅的“四时用药加减法”,示人方不可执,灵活应用。方书多说补中益气汤证应该口中和,不喜饮,也就是说口干、咽干是慎用、不用补中益气汤的。但李东垣在方后的之一个加减竟是“口干嗌干加干葛”。气虚当温补,实火当苦泻,虚火当清补,而李东垣的第二个加减法竟然是补中益气汤加苦寒泻火之黄柏和甘寒清补之生地黄。反思其治法,补中益气汤原方中只有“补其中,升其阳”之品,而缺少“泻其火”之药,加黄柏、生地黄似乎才成为完整的治疗脾胃内伤“始得之证”的补中益气汤。后世医家在使用补中益气汤时也多加减及合方使用,但灵活性远不及李东垣。具有代表性的加减有补中益气汤加茯苓、半夏,和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丸,读《薛氏医案》和《寿世保元》随处可见。脾胃不足,痰湿易滞,理应加茯苓、半夏;补中益气汤治“元气脾胃之虚”,六味地黄丸治“肾水真阴之弱”,“二方兼而济之,乃王道平和之剂”,合用似极为高明。但从李东垣“立方本指”去认识,则茯苓、半夏沉降有余,六味地黄丸降入下焦,皆不利于“升其阳”。可见,不解东垣本意,随意加减极易“动手便错”。误用极易坏事,于是后世医家提到了补中益气汤的禁忌症。如张景岳说:“元气虚极者,不可泄;阴阳下竭者,不可升。”柯琴说:“惟不宜于肾,阴虚于下者不宜升,阳虚于下者更不宜升也。”这些论述对后学者的临证是极其有用的。但从李东垣“立方本指”看来,这只是低层次的、形式上的认识。实际上,内伤脾胃病证中,肾虚完全是可以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的,只是用药时需斟酌升降浮沉。(高建忠山西中医学院第二中医院)
三、2022***5***31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气***眩晕医案
1、病史:乏力,下午开始头晕,下班回家乘坐地铁时出现后脑勺、前额头痛。平时经常右胁、中脘胀,气透不出,要深呼吸乃舒,心烦易怒,经常便秘。眠安,纳可。
2、月经周期27天,经期3天,量少,色暗,无血块,无痛经,有小叶增生。
3、全身畏寒,若下午说话多或用电脑时间长,有时会面热口干。
4、面色萎黄,舌尖红有点刺,脉弦细。
5、处方:人参粉(早上空腹吞服)8g,党参30g,白术9g,黄芪30g,当归15g,升麻6g,柴胡6g,葛根60g,天麻30g,白蒺藜30g,白芷15g,羌活9g,川连3g,石膏15g,生地15g,陈皮6g,7剂。
6、2010年11月17日二诊:服药的最初几天觉得内热,如口干小便热,几天后消失,自觉诸症大为改善。
7、精神较振,头痛、右胁中脘胀、气透不出、面热口干等症已除。
8、眩晕、畏寒减,眩晕的症状推迟到下班时才出现,心烦易怒好转。
9、11月11日月经来潮,5天净,量少,颜色较前鲜红。大便正常。舌尖红有点刺,脉弦细,面色好转。
10、处方:守上方,加生甘草5g,改白芷9g,14剂。
11、按语:患者年纪不大,症状可不少。而且,辨证属寒,还是热?是虚,还是实?
12、如果我们熟悉李东垣的阴火理论,会对本案的分析很有帮助。
13、阴火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中气不足,脾胃之气下流,一方面谷气不得升浮,心肺失养;
14、另一方面阴火起于下焦,上乘土位,表现为心火。
15、其次要机制是:阴火伤荣血,荣血大亏;
16、荣血大亏,又助长阴火,形成恶性循环。
17、故治疗需补脾胃、升阳气、泻阴火、补肺气、滋荣血。
18、李东垣创制的补中益气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是这一治法的代表方剂。
19、本案患者脾胃虚弱、中气不足,故神疲乏力、下午加重,到下班时更为严重;
20、右胁、中脘胀,气透不出,要深呼吸乃舒,是气机升降失司的表现;
21、心烦易怒、下班坐地铁出现后脑勺、前额头痛、说话多或用电脑时间长出现面热口干、舌尖红有点刺、脉弦,属阴火上冲;
22、便秘、面色萎黄、月经量少色暗、脉细,是荣血亏少;
23、全身畏寒,因谷气不得升浮,心肺失养,失于温煦。
24、以人参大补元气,党参、黄芪、白术健中州、补肺气。
25、升麻、柴胡、葛根、羌活、白芷引清气上升,参芪配当归滋荣血,川连、石膏降阴火,生地“补肾水,水旺则心火自降”,因“气乱于胸中”,用陈皮“助阳气上升,以散滞气”,又配天麻、白蒺藜治眩晕。
好了,关于补中益气汤加减医案和31补脾胃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